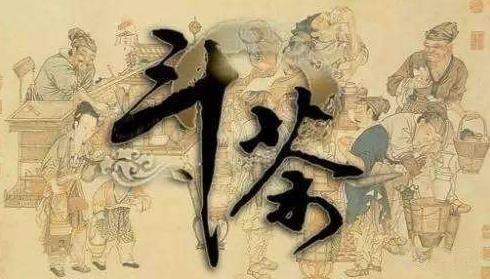
在宋代,茶文化繁荣昌盛,“斗茶”习俗风靡一时,而“天目”黑釉茶盏则成为这一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具,二者相互依存,共同谱写了宋代茶文化的精彩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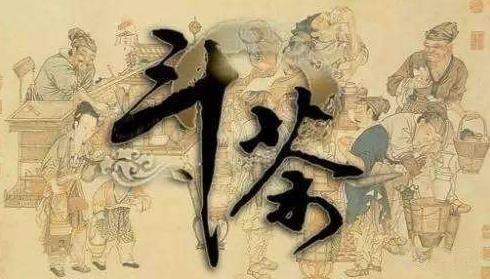
斗茶,又称“茗战”,兴起于唐末,在宋代达到鼎盛。当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对斗茶情有独钟。斗茶的流程颇为讲究,首先要将茶饼碾成细末,放入茶盏中,用沸水冲泡,随后用茶筅用力击拂,使茶末与水充分融合,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这击拂的过程力道需适中,既要让白沫均匀细腻,又要使其持久不散。
斗茶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是看茶汤的色泽,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依次递减,这与宋代推崇的素雅审美相契合;二是看白沫在茶盏上留存的时间,即 “水痕”出现的早晚,白沫保持时间长,水痕出现晚的则为胜。正如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所记载:“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
而 “天目”黑釉茶盏之所以能成为斗茶的首选,与其独特的品质密不可分。“天目”是对宋代福建建阳窑、江西吉州窑等烧制的黑釉茶盏的统称。建阳窑的兔毫盏釉面呈现出细密如兔毛的条纹,油滴盏则布满了闪烁如油滴的斑点;吉州窑的玳瑁盏釉色似玳瑁花纹,剪纸贴花盏则融入了民间艺术元素,各具特色。

图1 宋 建窑黑色结晶釉“滴珠”盏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黑釉茶盏的黑色釉面能够极好地衬托出茶汤白沫的洁白,使斗茶者能更清晰地观察茶汤色泽和白沫状态,符合斗茶的评判需求。同时,黑釉茶盏胎体厚重,导热性差,有利于保持茶汤的温度,延缓白沫的消散,为斗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图2 宋 建窑黑色结晶釉“兔毫”盏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建窑结晶釉黑釉茶盏的出现,为宋代文人间盛行的“斗茶”增添了新的乐趣。由于斗茶的风行,黑釉茶盏得到极大的发展,为此福建建阳的建窑脱颖而出,它所生产的黑色结晶釉茶盏,由于釉面有自然形成的各种结晶斑纹,而受到人们的宠爱。建窑黑釉茶盏的胎黝黑而坚,壁稍厚,釉色绀黑晶亮,器底露胎。据科学检测,建窑黑釉茶盏胎中氧化铁的含量通常为8%至9%,最高可以达到9.71%,釉中氧化铁的含量在7%至8%左右,最高达到8.68%。胎釉中较高的氧化铁含量,经高温烧造,原料中的部分Fe2O3,会还原成Fe3O4而放出氧气,并形成大量气体,以釉泡的形式存在。这些气泡吸附周围的铁矿物而在釉面排出,当这些气泡在釉面破裂时造成局部富铁。当窑炉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就发生液相分离,温度继续下降,就会因过饱和而析出赤铁矿(Fe2O3)、磁铁矿(Fe3O4)或者两者的混合物,这要看当时的窑炉气氛而定。当炉内温度较快冷却,这些富含铁的晶体就在釉面聚集成团,形成“油滴”,并且有强烈的金属光泽,史书上称为“滴珠”(图1),日本称为“油滴天目”。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油滴釉,釉面上铁的结晶主要以赤铁矿的形式存在,因此呈现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油滴釉,釉面上铁的结晶主要以磁铁矿的形式存在,就会呈现银色。当窑炉的冷却过程比较长时,会把这些富含铁的釉一起往下流动,产生一条条流动的痕迹,形成类似兔毫的流纹,有金属的光泽,在日本称为“禾木天目”。同样,在氧化气氛中形成的兔毫呈黄色,称之为“金兔毫”(图2),在还原气氛中形成的兔毫呈银白色,称为“银兔毫”。据最新研究,建窑银色油滴中的氧化铁析晶是高纯度的、罕见的ε-氧化铁晶相,兔毫的结晶也应该是如此。还有一种“曜变结晶釉”茶盏(图3),釉面不规则的结晶斑周围的光晕会随着阳光入射角度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十分珍贵,目前存世仅4件,都在日本,称之为“曜变天目”。

图3 宋 建窑黑色结晶釉“曜变”盏 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而名盛天下,北宋后期曾经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底足刻有“供御”“进盏”字样。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蔡襄的《茶录》中有“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句。苏东坡也热衷于斗茶,他有诗句“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说的都是建窑的“兔毫”盏。北宋陶谷在《清异录》中有“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说的是建窑结晶釉中的“鹧鸪斑”,应该是银色“滴珠”较大者(图4)。

图4 宋 建窑黑色结晶釉“鹧鸪斑”盏 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江西吉州窑除了生产黑釉复合加彩瓷器外,在南宋还生产兔毫、油滴茶盏。和建窑相比,吉州窑的胎质较细,胎色为浅黄或浅灰色,釉层也不如建窑那么厚,器物比建窑明显轻薄。
宋代的斗茶习俗推动了“天目”黑釉茶盏的发展,而“天目”黑釉茶盏又反过来助力了斗茶活动的盛行。它们不仅是宋代茶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美学的追求。如今,当我们欣赏这些古朴雅致的“天目”黑釉茶盏时,仿佛仍能感受到宋代斗茶场上那热闹非凡的场景,领略到宋代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之,2025-8-11